印度蒙兀兒王朝的開國君主巴布爾(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),在自傳中寫道:「費爾干納(Fergana)的另一個城鎮是奧什(Osh,今天中亞吉爾吉斯第二大城)……它氣候宜人,水流充足,春暖花開。關於奧什的美好說法有很多……安集延河穿過奧什周圍地區,然後流向安集延(Andizhan,今天烏茲別克東部一座城市,位在費爾干納谷地東南部)。在其兩岸都有花園,所有花園均可俯瞰河流。紫羅蘭很美,有水流動,春天時,許多鬱金香和玫瑰盛開,真是太好了。」
福音荒谷費爾干納
2019年1月底的冬天,我來到奧什,站在蘇萊曼山上(Sulaiman-Too Sacred Mountain,據說所羅門王曾來到這山上禱告、沉睡,這山又稱所羅門的寶座),我俯瞰這座當年巴布爾讚美的小城。小城故事多,但近代奧什最教人注意的,卻是1990年6月,當地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吉斯人為爭奪一塊集體農莊土地,爆發了種族衝突,非官方估計超過1千人死亡。
其實,奧什10公里外就是邊界,跨過去是烏茲別克(Uzbekistan)。往西走不遠,再跨過邊界,就是另一個中亞國家塔吉克(Tajikistan)。這一小圈的山谷巴布爾口中的「費爾干納谷地」,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,像打碎的鏡子,不只裂出3個國家吉爾吉斯、烏茲別克、塔吉克的國界,還分散出多塊的「飛地」(國中有小塊屬於別國的國土),以及複雜的種族、國土、利益問題。有人說,蘇聯瓦解,中亞五國在不情願之下獨立,他們不想俄羅斯離開,因為長期依附在老大哥之下慣了,獨立後國家經濟、政治、體制系統都必須靠自己。當權者也擔心,當人民從長期被壓制及管制下獲得民主,很容易被「自由」迷惑,膽子大起來,推翻政權。
蘇聯的結束,也使費爾干納谷地吹起宗教復興風,伊斯蘭宗教學校和組織團體紛紛冒起,興建學校又傳教,據說烏國建的宗教學校數量眾多,其中一半是建在費爾干納谷地的村鎮裡,伊斯蘭激進主義趁機而入,在地下活躍,使得費爾干納成了火熱的宗教溫床。2005年5月13日,這裡的安集延發生流血事件,烏茲別克政府與當地的伊斯蘭運動組織起衝突,軍方向抗議的民眾開火掃射,死傷慘重。費爾干納谷地,沒有巴布爾口中的鳥語花香,而是緊張血腥。
我有機會來到到奧什,近水樓台,當然計劃過去看烏茲別克的費爾干納谷地,甚至想再進前到塔吉克的第二大城苦盞(Khujand)。但時間關係,最遠也只是到谷地的首府費爾干納,在那裡度過三天兩夜。
前往費爾干納的路上

在我們眼中,吉爾吉斯人的外貌跟漢族差不多黃皮膚,但比漢族的輪廓深一些;烏茲別克人則是黃種人和白種人的混合體,有歐陸人外型。當從奧什越過邊界,我從查驗我護照的兩國官員臉上,看出不同。
進入烏茲別克的邊界,我與同行的友人尋找人共車,目的地是兩三個小時車程的費爾干納。有一對男女與我們共車,上車不久,男的突然打開手機播放伊斯蘭誦經祈禱,這時我和友人開始儆醒,改用馬來語溝通。我想,講中文或許不是最安全的,馬來語應該沒人聽懂吧?
這般提高警覺,乃是費爾干納一直瀰漫著保守激進的伊斯蘭宗教風,當地人一眼便能看穿我們是外國人,小心些是應該的。據知,烏國對宗教活動非常敏感,即使是主流的伊斯蘭教,也受官方監督、審查。中亞人眼中,基督教是俄羅斯人信奉的俄國東正教,跟身為穆斯林的他們是楚河漢界、壁壘分明的。
我們抵步入住在費爾幹納的公寓,外型看來像未建好的破樓房,一樓大門大開,旁邊有鐵籠子,籠外有幾隻大肥雞在溜達。走上樓,摸索一陣,才找到屋主瓦倫蒂諾一個在邊界開車的司機都知曉的俄羅斯女人。我們就只是向司機報了她的名字,就被送來她樓下。不同於外面的殘破,瓦倫蒂諾的屋子裡可是完美無瑕、溫暖典雅,一派俄國風。
一個俄羅斯女人,能在保守男性為主、強烈伊斯蘭風氣的城市活下來,開放自己的房屋出租給外國人,自然有其生存之道。踏入她屋子的入口走廊,穿過一排精緻的烏茲別克手繪陶盤,大大小小的,馬上讓人感受到烏茲的不同。相比周邊的斯坦國家們,烏茲別克更為顯眼,一來它在絲綢之路上有很多昔日的伊斯蘭遺跡,二來烏茲的傳統手工藝如繪畫、養蠶作絲、手繪陶瓷等都別具一格。離開瓦倫蒂諾的公寓往外走,我們又彷彿走在昔日的蘇聯。蘇聯已逝,但它高度集中權力、冷冰冰又不帶情感的管理體制,留下的影響還是顯而易
當我們要把福音帶入中亞,能不能先站在當地人的角度,思考他們受過的政治衝擊,以及伊斯蘭教規的影響?福音,對中亞人來說也是近幾十年的「新東西」,若沒有禱告聖靈的帶領和靈風吹拂,在百般陌生和無知之下,硬土是無法打開的。
改變正在發生
烏茲別克有3,300萬人口,福音派基督徒占人口不到1%。根據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(US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, USCIRF)報告,2019年間烏茲改善了宗教管制,政府立法禁止執法人員隨意突襲及騷擾宗教社區。Johannes Reimer,世界福音聯盟的「和平與和解網絡」主任受訪時說,目前烏茲政府登記了54個不同宗派的基督教會,也支持一些公開的福音活動。該年9月,18個宗派的福音教會首次組織成聯盟,彼此合作、聯合禱告、傳福音。通常,這些教會各有俄羅斯、西方或韓國式的風格。它們的聯合,形成強而有力的聲音,也改善了當地人對福音教會的印象。
烏茲的福音教會可以分成20個大支派及附屬的小支派,除了在蘇聯時代留下來講俄語的傳統教會如浸信會、五旬宗,現還有混合不同中亞族群及語言的新型教會。而當地的韓裔更是高度福音化的族群,在一些地方更有強大的韓國長老會。
但是,我無法知曉烏茲的費爾干納這一帶有沒有基督徒?我和友人早上逛農業市集,也是相當「受歡迎」的。我手抓相機,一排排賣馕的婦女對此感到好奇。友人嘗試講一些俄語,比手劃腳的溝通,婦女們拿大如月亮的馕給我拍照。她們相當白皙,雙眼像畫了黑眼線,也不怕陌生人。我走到麵包店,搓著麵包的男子有著淡褐色的短髮,看我要拍照就露嘴一笑,幾顆金牙跑了出來。市集還有兩個大男人,蹲坐著,有著彪悍的雙眼,但他們只是賣葡萄藤的農民。
年輕人對未來徬徨
晚上,我和友人走去購物街時,被一個少年人截住。他很迫切地開口問我們會說英語嗎?他很想跟我們說英語。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問題,怎麼會有人攔住人只為了練習說英語呢?他說得不夠流利,便說他有位朋友能說得更好。這位朋友來了,看來十八二十歲。我們站在超市前的一個走廊,聊呀聊的,就整個鐘頭過去。交談之下,他說出了對這裡的生活及未來感到沮喪,覺得沒有出路。他渴望到英國讀書,賺大錢。

天曉得他把英國想像成什麼樣子呢?但他有如此憧憬也不奇怪,也反映了現代烏茲年輕人的心靈實況。外面自由世界對他們有很大的吸引力,但是,一旦獲得所謂的世俗、物欲和民主,他們又或許會受到衝擊,或自卑,或自大,重新披上自己過去的伊斯蘭族群身份,成了極端的民族主義者,以自己過去在伊斯蘭教義下受的不自由,反擊這個世界的自由。
離開費爾幹納那天,我們回程的司機也是一個很渴望跟我們交談的年輕男子。他英語真的有限,便用手機找了朋友來翻譯。這位朋友叫費斯拉丁,英語說得通,講了兩下,他就要求我把他加為臉書朋友。在這個封閉的谷地,他們對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。那麼,他們有機會遇到福音嗎?
在各種限制下,中亞的基督徒是以「生命影響生命」換來信仰的。回到奧什,我和友人來到蘇萊曼山。山下有座巨大的清真寺,有個戴了黑色絨帽的老人倚著拐杖,伸手出來跟友人講話。老人說,要跟隨阿拉啊!老人也真的會抓著機會傳教。我們只能對他微笑,然後就信步走上山了。有一群老老少少的婦女這時也上山。她們對著我的相機鏡頭笑笑,一位中年婦女露出金牙。我問她為何上山?她說要拜拜喔!
原來蘇萊曼山是當地的聖山。在伊斯蘭教傳入前,這裡有拜火教等異教活動。山上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洞穴,更有早期留下畫有人類、動物及天體的岩石刻畫。婦女們上山,是要到洞穴裡祈福,比如早生貴子、治病、求長壽等。在山頂及另一邊的山腳,也各有一座供奉死去聖人的陵墓。生活中,人很難離開對各種未知神靈的膜拜,膜拜中也充滿恐懼、不安。屹立千年的蘇萊曼山,見證了奧什人生命上的無助,但它對人的救贖,也無能為力。
不過,主的福音活水已經流入奧什。一天晚上,我們與數位宣教士見了面,參與他們的禱告會。冰冷的寒夜,大家聚在溫暖的客廳,有些人帶了點心,主人家則泡了茶。我們彼此問候後,便低頭安靜下來。有人開始唱詩,唱起了主的美好,有些人不自禁的舉了手。宣教士一個接一個為接觸到的人禱告,求主開他們的心眼,好教他們回轉信耶穌。聚會結束,夜深人靜,屋外只有黃澄澄的街燈。這時,周圍瀰漫著煙霾,是冬天燒煤取暖的煙霾。我們坐著一位宣教士的車子回旅館。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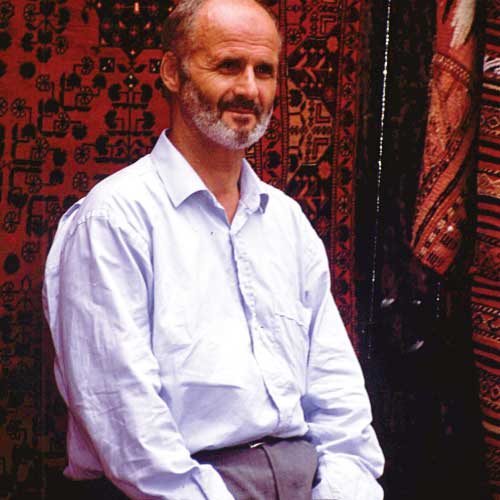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美國
美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