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是受難與復活節,我們鼓勵讀者本月讀完整卷馬太福音,每天以禱讀方式靈修,默想其中一節,將經文化成禱告和行動。
本月禱讀資料由夏超凡牧師撰寫,特此致謝。

梅干,是許多人對日本文化的味覺印象。
當梅干輕輕落在舌尖,強烈的鹹味瞬間衝擊味蕾,鹹味漸漸退卻後,酸味隱隱浮現,令人不禁皺起眉頭。鹹與酸之間,一絲淡淡的甜味悄然而至。
品味梅干,彷彿在細嘗日本社會的百種滋味。那片濃烈的集體意識撲面而來,隨之浮現的是日本人在巨大齒輪下的生活辛酸,以及深藏於社會隙縫中甘甜細膩的人情味。開始為日本禱告前,我們懷着尊重的心,先來一顆梅干吧!


梅干,是許多人對日本文化的味覺印象。
當梅干輕輕落在舌尖,強烈的鹹味瞬間衝擊味蕾,鹹味漸漸退卻後,酸味隱隱浮現,令人不禁皺起眉頭。鹹與酸之間,一絲淡淡的甜味悄然而至。
品味梅干,彷彿在細嘗日本社會的百種滋味。那片濃烈的集體意識撲面而來,隨之浮現的是日本人在巨大齒輪下的生活辛酸,以及深藏於社會隙縫中甘甜細膩的人情味。開始為日本禱告前,我們懷着尊重的心,先來一顆梅干吧!

日本貧困危機觀察
中年人的貧困
這群人是日本泡沫經濟時期畢業的大學生,俗稱「就業冰河期一代」。由於日本企業偏好社會新鮮人,他們錯過了入職最佳時機。如今已至中年,仍是打工族或派遣員工。健康狀況像個定時炸彈,一旦爆炸,就會跌入無底深淵。
英國社會學家提出多項衡量「相對貧困」的指標,例如是否有能力購買家電、負擔教育費用、偶爾外出用餐、維持基本社交生活等。一般而言,當收入低於該國平均收入時,即屬於「相對貧困」。
「絕對貧困」是指無法滿足生活基本需求,包括收入低、營養不良、健康狀況惡劣及無法接受教育等。
浮世繪與印象派畫廊
喜多川歌麿、葛飾北齋和歌川廣重被譽為「浮世繪三傑」,是日本藝術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。喜多川歌麿筆下的美人,一顰一笑皆靈動傳神;葛飾北齋與歌川廣重的風景花鳥畫作,猶如一張張旅行明信片,以獨特的視角捕捉江戶時代的名勝風光。這3位大師的作品不僅在日本本土備受推崇,更主導了西方世界對浮世繪的理解。
文藝復興以來,西畫追求呈現三維空間、色彩與形態的和諧。日本浮世繪的出現,像一記重錘撼動了這個傳統。浮世繪以平面色塊的塗染技法、二維的畫面處理,以及大膽的不對稱構圖,啟發了一群西方畫家擺脫寫實主義的束縛,轉而探索抽象的表現手法,促成印象派與後印象派的誕生。
▲ 喜多川歌麿
《當時三美人》是美人繪大師喜多川歌麿的經典之作。眼角的溫柔、秀麗的鼻梁……畫家細膩刻畫了江戶時代最負盛名的3位美人,將她們各自的神韻拿捏入微,充分展現了這位美人繪大師爐火純青的畫工。
▲ 愛德華 • 馬內
平塗色彩是浮世繪的一大特徵,此繪畫技法最早被法國印象派畫家馬內應用。《吹笛子的少年》中,馬內將人物置於單調的平塗背景前,刻意淡化傳統西畫的立體空間感,捨棄明暗陰影與視平線的表現。畫中少年紅色褲管的黑色輪廓線,幾乎完全承襲浮世繪的線條,巧妙地使人物從背景中凸顯而出。
▲ 葛飾北齋
《富嶽三十六景.神奈川沖浪裏》是舉世聞名的日本浮世繪作品,葛飾北齋以富士山為背景,描繪神奈川沖的巨浪翻捲着漁船,漁民們努力生存。套印使用了從歐洲進口的顏料「普魯士藍」。
▲ 歌川廣重
歌川廣重出自江戶時代的最TOP藝術社團——歌川派。《名江戶百景.龜戶梅屋舖》放大局部枝幹,將名勝風景龜戶梅屋舖安排在遠處,此構圖手法深深征服了梵谷的心,他以油彩臨摹了一幅《開花的梅樹》(右圖)。
▲ 文森 • 梵谷
浮世繪作為畫中畫,成為印象派畫家筆下常見的創作元素,《唐吉老爹》即為代表。後印象派大師梵谷迷戀着浮世繪,他私藏超過600幅浮世繪,反复臨摹。與胞弟通信來往中,梵谷無數次提及嚮往日本:「我全部的作品,在某種程度上,都奠基在日本藝術。」
日本與基督教的距離
這片基督徒人口僅占1%的土地上,日本與基督教的距離沒你想像得那麼遠。早在16世紀末,葡萄牙傳教士沙勿略開啟了日本與基督信仰的第一次親密接觸。日本基督教並未局限於傳統的布道模式,而是不斷發展出多元且富有創意的福音策略,與日本平凡又溫暖的日常融為一景。


❶ 神奈川縣藤澤市
衝浪事工「Wave of Grace」
鵠沼海岸的銅像前,矢部先生搭起了一座小帳篷。每逢週一和週五,這座小帳篷便會如約出現,成為衝浪客的補給站。帳篷裡不僅提供飲料、充電器和衝浪板,更給矢部先生與衝浪客建立關係,甚至吸引了喜歡衝浪的牧者前來聚集交流。

❷ 無固定地點
東北亞基督教文學會議
日韓輪流主辦的文學交流會議,旨在促進兩國基督教文學研究者的互動,並從彼此的視角反思文學。儘管許多日本文豪如芥川龍之介、宮澤賢治等並非基督徒,但他們的作品字裡行間卻蘊含了基督信仰的精神。透過文學研究,基督徒學者可以發掘福音與文學的連接點。

❸ 宮崎縣仙台市
餐車事工「心之廚房」
「心之廚房」每週固定在兩處營業,同時每月參與街友關懷事工,期盼透過料理與人連結。這是個剛剛起步的服事,願宣教日引讀者以禱告默默守護「心之廚房」。

❹ 宮崎縣多賀城市
食物援助「生命之糧」
「生命之糧」主要事工為發放食物包,支援弱勢群體的生活。他們定期去好市多領即期麵包,再由宣教士登門拜訪,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。發放食物的同時,宣教士不只關懷人們的生活需要,更把握機會為他們禱告。

❺ 宮崎縣仙台市
弱勢群體生活支援
「Operation Blessing」國際福利團體與當地教會、差會攜手合作,每月在勾當台公園舉辦關懷活動。他們不只發放「心之廚房」預備的便當和生活物資、獻唱詩歌,也協助街友申請就業及租屋。這些陪伴不僅改善街友的生活處境,更讓當地居民信任教會,為福音撒種鬆土。

❻ 茨城縣利根町
基督祭典
日本人熱愛祭典。然而,祭典往往涉及祭拜神明的宗教儀式,教會多半迴避。利根基督教會卻另闢蹊徑,舉辦「基督祭典」(キリ祭り),巧妙運用日本人熟悉的祭典形式,吸引許多路過的大人小孩走進教會,與會友和牧師自然交流,為教會與社區搭建福音橋梁。

❼ 茨城縣利根町
舞蹈教室
只要把講台遮起來,這裡就是舞蹈教室。由於親戚擁有舞蹈專業背景,牧師靈機一動,想出了絕妙安排。日本人普遍對宗教存有戒心,靈活的空間運用,沖淡了宗教色彩,會友能以舞蹈教室的名義,邀請人來教會。

❽ 日本各處
語言學習
語言學習是宣教場上歷久不衰的傳福音策略。日本除了常見的英語教學,韓語教室也漸趨普及,這與眾多韓國宣教士在此服事有關。另外,由於本土牧者不足,不少日本教會由韓國牧者牧養。

❾ 東京都東村山市
免費運動場
日本的免費運動場地少,這成為國際宣教會(One Mission Society)的宣教良機。他們將教會空地規畫為運動場,開放給附近居民使用。由於場地毗鄰神學院,成為會友、神學生與居民交流的絕佳場所。國際宣教會透過Line管理運動場,適時將福音活動訊息推播給常來運動的居民。

❿ 東京都新宿區
酒吧教會
除了婚禮,鮮少日本人願意踏入教會。面對這樣的現實,中村牧師走進酒吧,當起了調酒師。牧師每晚兩次的短講,成為這間酒吧的獨特風景。在這裡,人們卸下厚重的面具,傾吐心裡話。雖然酒吧座位有限,卻是一處溫馨、敞開的地方。(見4月14日內文)

日本宣教史3個重要時期
Period 1
歐洲發現日本 1549~1612年
當馬丁路德向羅馬教廷提出改革訴求之際,天主教內部也掀起一股革新浪潮——以依納爵和沙勿略為首的宗教領袖在法國創立了耶穌會,立志過着貧窮、貞潔的生活,並向外宣教。
這時適逢歐洲大航海時代,葡萄牙、西班牙的商船頻繁往來東方。1540年,沙勿略把握時機,跟隨商船,開啟亞洲宣教旅程。他在旅程中偶遇一位日本武士,心裡萌生前往日本的想法。
1549年,沙勿略抵達日本鹿兒島,在九州、山陰山陽、近畿等地展開傳教活動。他是日本拓荒宣教先鋒。此後,各天主教修會的傳教士紛紛追隨歐洲商隊的腳步,來到這片福音貧瘠之地。
福音種子很快地在日本開花結果——數十位大名註受洗,近百萬平民成為信徒,約占當時日本總人口4%。宣教如此成功,主要有兩大關鍵因素:首先,歐洲商隊帶來了步槍、火藥、織品等日本急需的物資;其次,傳教士謹守清貧的生活作風,積極投入慈善工作,贏得地方大名的支持。
然而,福音盛況最終招致當權者的反感。1612年,德川幕府頒布禁教令,為這段宣教黃金時期畫下句點。
註:日本戰國時代的封建領主稱呼。
Period 2
上帝VS.天皇 1873~1945年
明治政府成立之初,雖然延續了德川幕府的禁教政策,但在西方列強的施壓下,不得不改弦易轍。1873年,日本廢除禁教令,開始積極吸收西方先進思想與文化。而各大基督新教教派紛紛派遣具備醫療、教育等專業背景的宣教士前往日本,因此宣教成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知識分子階層。
基督教的發展沒多久就遭遇嚴峻挑戰。1890年,愛國主義思潮興起,當局相繼頒布了《大日本帝國憲法》、《教育敕語》、《小學校祝日大祭日儀式規程》等法令,要求人們在學校喊天皇萬歲、向《教育敕語》行禮,強化天皇的神性,剝奪人民的宗教自由。
面對西方列強虎視眈眈全球,日本政府為求自保,積極向外擴張,同時在國內肅清異己,禁止反戰言論、逮捕外國宣教士,並強制組建日本基督教團,要求教會與政府合作。日本基督徒載浮載沉,教會活動日漸蕭條,信徒人數銳減。
著名的日本基督徒知識分子
內村鑑三
在課堂上拒絕禮拜《教育敕語》,引起撻伐。
海老名彈正
曾用演說、布道,主張日本向外擴張是為義而戰。
新島襄、新島八重
創立基督教同志社大學,在課程中帶入基督信仰。夫妻兩人都是日本重要的教育家。
Period 3
澆熄的火苗 1945年~
1945年日本戰敗後,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負責整頓百廢待興的日本社會。他修改憲法,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,日本天皇也脫去神格。
由於麥克阿瑟的親基督教政策,以及美國、加拿大宣教機構的援助行動,日本基督徒人數穩定增加。可惜這波宣教熱潮以援助為前提,信仰根基未能扎穩在日本人的心土上。
1954年,美軍的核爆實驗導致日本漁船遭受輻射傷害,澆熄了這波宣教熱潮。這起事件在日本社會掀起強烈的反美情緒,也間接影響民眾對基督教的態度。自此之後,日本基督徒人數逐年下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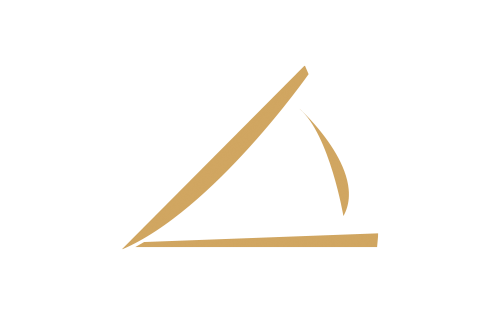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 美國
美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