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师母2024年回天家后,我常常想念她。这一年,虽然宣教日引的事工依然持续推进,除了怜悯关怀事工稍微放缓,其他事工基本如常,表面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然而我们心裡都清楚,一切不再一样。过去是师母默默地稳住方向,把每位同工的心连结起来,推动整个团队朝着目标稳健前行。现在,我们失去的是团队的轴心。
这一年,每当我需要抉择,或回应各种需要,总是想如果师母还在,她会怎麽做?她会说什麽?我下意识地学她,做她会做的事。比如,她会坚持为未得之民祷告,从不缺席祷告会,每一次祷告都情词迫切,打从心底爱这些灵魂;遇到同工面对困难,她必定认真代祷、跟进,并付诸实际行动;与同工配搭时,我会记得师母视同工的成长和感受,比事工本身更重要,总是选择等候与陪伴,也亲自支援帮助同工完成工作。还有,她会以宽广和利他的心,与其他机构配搭。我一点一点学她,虽然我与她的差距很大,但她是我学习的方向。
一天,我读约书亚记11章,圣灵肯定我的方向:「师母是摩西,你是约书亚;她是pioneer,你是接续者。你学她,是对的。」我突然想起15年前,师母找我接任宣教日引主编,她说:「我不是要找一个编宣教日引的人,我要找接棒人。」于是,我搞清楚了自己的角色,就是把师母领受的异象传承下去,为未得之民祷告是来自神的呼召,值得和必须传承下去。我感恩师母忠心完成了她的角色,并且把美好的祷告生命传承给我,过去那15年我和她一起祷告的经历,是她留给我最重要的遗产。
约书亚记前半段详细记录了4场主要战役:耶利哥城、艾城、南方五王与北方诸王。以色列人从失败和得胜的经历,学会了作战的关键模式,就是「倚靠神,神就出手帮助;百姓顺服神,敌人便被消灭」。当他们掌握了这属灵原则,圣经不再逐一描述后续的战役,而是用一句话总结:「约书亚和这些王争战了许多日子。」(书11:18)
同样,宣教日引走过9千多个日子,在师母的带领下,也是在「对的模式下做对的事」,在平凡日子的循环裡,忠心出版每一期。有一次祷告会,梅兰牧师分享说:「我还不是同工之前,就已经是宣教日引的读者,我很感恩,25年来从未有过一期停刊。」以后,我们将继续在「对的模式下做对的事」。
当我再读约书亚记12章时,更深领受「传承」的意义。这章总结战绩时,提到摩西击败了两位王,而约书亚则打下了31位王。从数字上看,约书亚的战绩似乎更耀眼,却是摩西前期的开荒,以及在旷野长年陪伴与栽培,为约书亚奠定重要基础。摩西忠心完成了神交付的任务,把使命与异象清楚传递给约书亚,使他承接并完成后续的呼召。
真正的传承,不仅是交棒,更是把异象与核心价值讲明,让下一代知道该如何继续回应神的计画。感谢神,师母患病前的几个月,圣灵特别感动她,把宣教日引的核心价值清楚写下来,使我们如今有清楚的方向承接异象。神不要我们停下脚步,祂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
摩西把呼召和使命传承给约书亚,但约书亚没有传承者,宣教日引要引史为鑑。
「约书亚在世的时候,以及他去世以后,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众长老还在的日子,众人都事奉耶和华……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的列祖那裡以后,有另一代的人兴起来了;他们不认识耶和华,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」(士1:7、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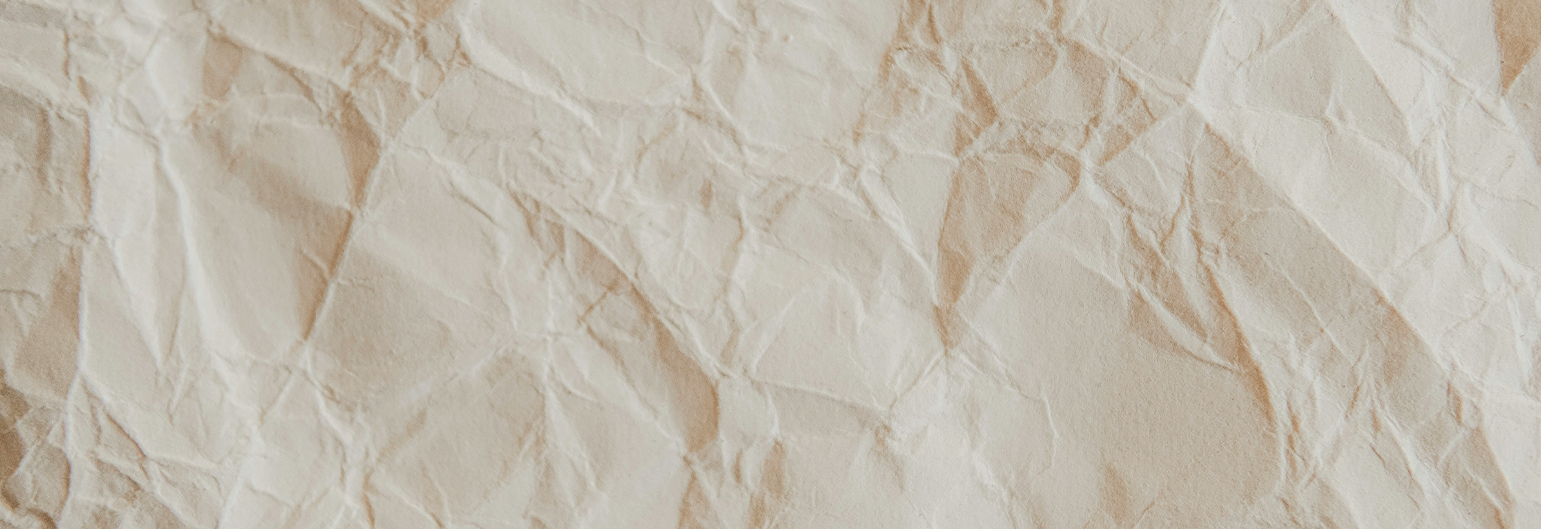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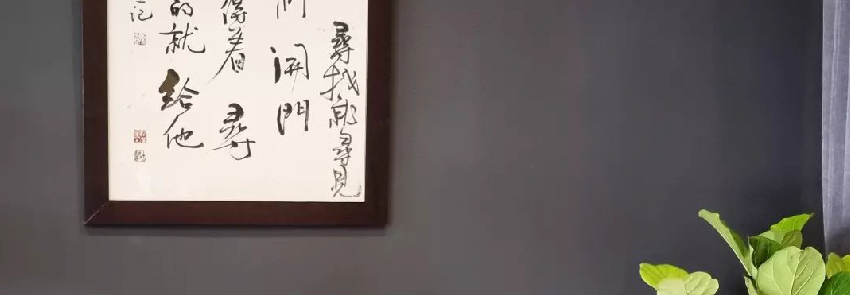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 美国
美国